特朗普政府执政后期,美国商务部陆续将250多家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拜登政府继承了前政府对华技术管控的思路,在高科技领域采取“小院高墙”的封锁措施,并未放弃对实体清单上中国企业的管控。然而,数年时间过去了,美国的出口管制措施对中国企业的实际影响如何?笔者通过检索发现,这些被列入清单的中国企业的经营发展状况存在着天差地别。
10月29日,华为发布2021年前三季度经营业绩。前三季度,华为公司实现销售收入4558亿元人民币,同比下滑32%。公司7月底推出的高端智能手机不支持5G,而且还被迫出售部分业务。根据华为董事长徐直军更直言,未来五年,该公司唯一的目标就是活下来。

然而,大部分实体清单上的中国企业并未受到美国出口管制政策太大的影响。
比如国内最大最先进的晶圆代工厂中芯国际于2020年10月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但其业绩却反而随着全球的“芯片荒”而一路高歌。中芯于2021年11月11日发布了Q3季度财报,运营收入92.8亿元,同比增长21.5%,实现净利润20.77亿元,同比增长22.6%,前三季度实现净利润73.18亿元,同比增长137.6%。
而海康威视被列入实体清单的时间更早,2019年10月即被美国列入清单。根据其刚刚披露的2021年三季报,前三季度,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超过550亿元,同比增长超3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66亿元,同比增长接近30%。前三季,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创历史新高。那问题是,为什么同是实体清单上的列名企业,华为受到的影响就格外大,而其他上榜的中国企业却业绩创下新高呢?
经过笔者的研究和分析,美国政府对不同中国企业出口管制的政策法规其实并不一致。在规则制定和现实执行中,美国政府商务部和国会立法者都将扼杀华为获得5G和其他高科技软硬件设备作为第一要务,其歧视性政策可见一斑。而对其他的实体清单企业,美方的执法和调查资源有限,特别涉及在华调查问题上缺乏一般途径。美国商务部主管出口管制的部门工业与安全局(以下简称“BIS”)在执法上只能“抓大放小”,几乎将主要精力都放在华为一家。
01 华为明显受到美国政府的“区别待遇”
首先,华为即使在所有的实体清单列名企业中也是被美国政府区别待遇的。美国政府对华为的出口管制那是拳拳到肉,毫不留情。BIS可是用尽了十八般武艺,特别两度修改了美国出口管制的法规,为华为及其子公司设置了新的规定,唯一的目的就是堵住华为获得美国技术和产品的一切通道。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电子消费品生产国和消费市场之一,而华为在全球有着无数的实体,如何能够有的放矢地打击到华为,同时尽量不伤害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和整个供应链中的地位,把握这个平衡对BIS来说非常困难。为了完成这个政治化的目标,BIS对美国的出口管制体系作出了重大的调整,不惜为了对付华为这一家公司而修改整个出口管制法规。
2020年8月17日,BIS直接针对华为及关联公司再次定向修改了“外国直接产品规则”(Foreign Direct Product Rule,简称FDP规则)。该修订扩展了美国出口管制法律对涉及华为供应链的全面限制。什么是FDP规则呢?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引入一个助手芯片小黄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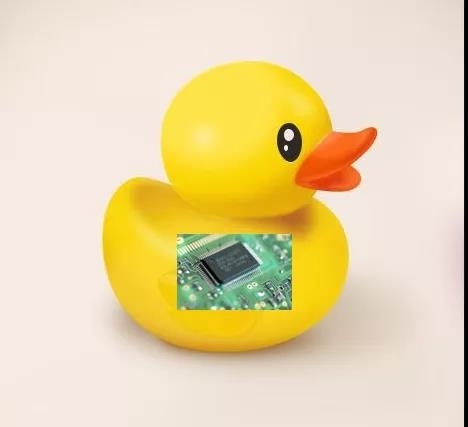
假设华为不能直接买美国芯片,于是有家中国生产小黄鸭的中国企业挺身而出,“这样吧,美国高通把5G芯片卖给我,我把芯片装到我生产的小黄鸭肚子里,然后再把芯片小黄鸭转卖给华为不就好了。这样芯片小黄鸭属于Made in China的中国产品,转卖也不用美国人管了吧。这份罪我受了,这份钱我也挥泪赚了”。
美国的出口管制法为了防止这种漏洞的出现,制定了两个规则,第一,最低成分规则,第二“外国直接产品规则”。最低成分(通常是25%),意味着美国受管控产品的最低价值必须小于25%,这件商品才可能豁免管制。这里芯片价值远远高于小黄鸭价值,则出口管制条例依然将管制芯片小黄鸭。第二,就是“外国直接产品规则”,在BIS专门为华为量身打造之前,美国出口管制条例(EAR)规定,“外国产品”即非美国制造(Non-US made)的产品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受到美国出口管制法律的管辖。对你没听错,哪怕是在中国本土生产的商品,只要符合EAR的限制规定,美国人认为自己仍然可以管。当外国厂家进口了美国产品,重新组装销售给下家,这种行为可能被定义为出口管制法规下的再出口(re-export)。
是否会被美国监管,在“外国直接产品规则”修改之前,只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该产品若是使用美国软件或技术生产的直接产品,或利用美国技术或软件的工厂或设备生产的直接产品。而该美国软件或技术是因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原因而受到出口管控的;同时该非美国制造的产品本身也被列入管控商品清单(Commercial Control List),且因国家安全原因受到美国出口管控;另外,上述产品的出口目的国必须为国家组别(Country Group)中 D:1或全面制裁(E类别)的国家。
也就是说,若适用外国直接产品规则的非美国制造的产品受到EAR管辖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涉及的美国软件或者技术受到特定原因的管控,(2)非美国制造的产品受到特定原因的管控,以及(3)特定的最终目的国不属于D1。
根据上述修订前的规定,若三个条件不能同时满足,则外国产品可能就不受美国出口管制法律管辖。如果产品满足前两个条件,但最终目的国不在上述特定国家组别之列,则该产品不会受到EAR管辖。
例如,一个使用美国软件在英国生产的5G芯片,而上述美国软件与英国产的5G芯片均因国家安全原因受美国出口管控,但若最终出口目的国是澳大利亚(不在D:1/D5,E:1, E:2之列),只要该英国芯片的美国成份含量不超过25%,即最低成份规则(De Minimis Rule),则该芯片将不受到美国出口管制法律的管辖。
好,现在魔法来了。依据修订前的国外直接产品规则,在澳大利亚的华为子公司即使已经被列入实体清单,若购买案例中的5G芯片仍然不会受到任何限制。因为美国成分的含量已经低于最低成分标准,不属于被美国监管的对象。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要修改实体清单规则的原因。华为在海外有诸多子公司,可能会利用这个漏洞而依然可以获得美国的芯片。
02 美国两次修改涉及华为出口管制法规
为了彻底打死华为,BIS为华为量身定做了一套法规。这套法规经过两次修订。
2020年5月美国工业安全局开始了针对华为的规则修订,针对当时已经被列入实体清单上的69家华为企业(包括68家非美关联公司)修订了外国直接产品规则。这次修订在外国直接产品规则下直接将矛头指向华为。于是,实体清单企业分为了两种类型,一种是其他企业,一种是华为。
首先,新规适用也仅适用于在实体清单中的华为及关联公司。因为,根据法条规定,新规则仅指出适用的实体是实体清单中包含在新的脚注1的实体,而现阶段,只有华为及其关联公司在脚注1项下。
第二,原规则下第(3)项最终目的国的要求不再是一个决定因素。
第三,外国企业知道或应该知道其生产的物项运送至在实体清单上的华为及其关联公司。这里要求主观上的故意,其实也是为了误伤“美国队友”,很多时候,有些东西卖来卖去就不知道下家了。
第四,新管制规则采用了涵盖两类外国生产物项的更为宽泛的控制标准。
第一类物项是列入实体清单的华为及其关联公司生产或开发的外国制造的物项(如集成电路设计),这些物项是受EAR约束的部分软件或技术的直接产品,并因“国家安全”原因受到管控(如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
这个条款不好懂,给大家举个例子。例如,某个美国境外的晶圆代工厂在运营中虽未采用受管制的美国工具或器械,但是其获得了华为某个芯片设计图,要求按照该图代工。而该项设计是相关的 EAR 管制技术或软件的直接产品,并且该晶圆代工厂被要求将基于此生产或开发的物项转让给华为。这里的芯片成品则也会被要求接受美国的管制。
第二类是指外国制造的物项,这些物项指美国境外工厂或其主要部分的直接产品(包括半导体制造设备),而该工厂/主要部分本身是受EAR项下CCL第3、4、5类约束的部分软件或技术的直接产品,而且外国生产的物项是华为生产或开发的软件或技术的直接产品。该规则覆盖了出口管制分类编码(ECCN )中3E001、3E002、3E003、4E001、5E001、3D001、4D001或5D001中列示的美国原产技术或软件;和3E991、4E992、4E993或5E991中列示的美国原产技术;及3D991、4D993、4D994或5D991中列示的美国原产软件。
这里其实含义是只要涉及上述编码的技术、软件,是没有最低成分规则的。而这里编码背后的产品和技术非常广泛,涉及到主要的先进电子技术和产品,其目标还是阻碍华为在芯片研发技术上有突破性进展。
第二次修订
2020年8月17日美国工业安全局再次针对华为对相关管控规则进行了扩展和修订,进一步扩大了“外国直接产品规则”对华为及其关联公司的覆盖物项范围。“外国直接产品规则”不再局限于华为开发或生产的外国制造的物项。取而代之的是,当出口方知道或应当知道以下情况时,外国制造的物项将受“外国直接产品规则”约束,并需要获得许可证:
1. 物项将被置于或用于“生产”或“开发”华为生产、采购或订购的任何“部件”、“组件”或“设备”;或
2. 华为是涉及外国生产的物项的任何交易的一方,包括“购买方”、“中间收货方”、“最终收货方”或“最终用户”。
也就是说,只要外国制造的物项在供应链中任何环节涉及实体清单上的华为及关联企业,则适用于新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则,也就是需要向BIS申请许可证。
说了这么多,这么复杂的规则都是针对华为一个公司的。
03 对华为采取严厉的执行措施
平心而论,在这样强势的镇压下,华为还能取得这样的业绩已经很不错了。可俗话说,不怕官,就怕管。虽然其他企业被列入了实体清单,但是美政府在涉及华为的执法问题上更是分外用心,明显有特殊“照顾”。
11 月8 日, BIS因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叫SP Industries科学设备制造商于2019 年向华为和海思科技非法出口商品而处以 8 万美元的罚款。这家名为 SP Industries 的公司在中国科技公司被添加到实体清单后,仍向它们出口了价值超过 170,000 美元的商品。其实这个贸易体量很小,产品的技术水平也很低,说白了也就是因为和华为贸易,BIS才对其痛下狠手,明显是杀鸡儆猴。
除此之外,最近BIS因为对希捷公司与华为的贸易调查缓慢而被国会议员diss了。甚至国会大爷们就此专题,特别撰写了一个报告,大骂“勤勉”尽职“的BIS工作不到位。而事实上,BIS就差来深圳龙岗守夜了。
04 总结与建议
虽然,目前除了华为以外其他的实体企业经营状况尚可。但是美当局对华的技术管制措施可谓其对华遏制战略的核心。未来对华加强出口管制执法措施的趋势将继续加强。因此,可能会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受到BIS执法的负面影响。
今年10月, BIS代理副部长杰里米·佩尔特(Jeremy Pelter)表示,与去年相比,今年对华出口管制的执行和处罚力度激增,企业因涉嫌违法出口管制至中国的案件数量也大幅增加,BIS所开出的罚金也大幅增加,到9月份已经达到了约600 万美元。针对美国企业涉华出口违规案件,该机构在2021财年期间开出了约186万美元的刑事罚金和超过400万美元的民事罚金,远远超过2020年约6万美元的罚款总额。在刑事层面上,BIS在2021财年,对所有涉华出口人员共提出了高达226个月刑期请求总量,而这个数字在2020财年提起的总的刑期只有80个月。佩尔特最后还强调了,BIS的执法分析师和特工将继续针对试图混淆最终用途和最终用户以规避出口管制限制的行为进行打击,以防止窃取敏感美国技术信息的企图。
因此,往后看,中国企业面临的美国出口管制风险越来越大。除了华为生产链上有关的企业暴露在BIS的监管下外,其他的企业也可能面临美国强化的监管。
在芯片、医药、互联网和其他敏感技术领域的企业和这些企业的供应商都应该立即着手自查、评估,尽快做出调整与应对措施。根据新规则,建议和华为有关系的中国企业也采取以下措施:
1.筛查外国制造的产品中是否含有美国原产软件或技术
企业可以根据业务特点筛查在生产、设计或加工等各个环节是否直接或间接的使用了美国原产的软件或技术。有些美国设备比较容易记得,但是美国原产操作系统软件特别是工业母机的软件就容易忘却。这需要特别注意。
2.有哪些产品受修订后的EAR规则限制
根据修订后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则,若使用了美国原产软件或技术,只要供应商知道或应当知道其产品是向华为及其关联公司(已被列入实体清单的)直接提供或间接用于生产或开发华为所采购的部件、组件等产品,均受外国直接产品规则约束,即受EAR管制。所以
3.涉及华为的交易供应链和分销渠道重新评估,这里对华为的制裁其实包含了其他的贸易环节,有必要做更详细的重新估计
4.关键还在于公司内部的合规制度重新评估
涉及美国技术和产品的企业应该建立起跨境的合规体系,通过实时更新的内部合规制度来降低企业受到美国出口管制法律法规制裁的风险。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
 关注公众号
关注公众号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